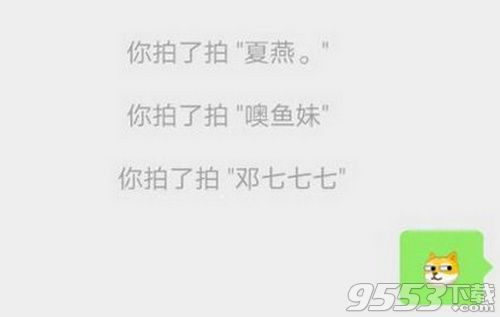县二中的孩子:不会“做题”,只能被剩下?
县二中的孩子:不会“做题”,只能被剩下?
作者 | 斯通纳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编辑 | 晏非
题图 | 视觉中国
在陕西省某县中念初中期间,蒋黎明的妈妈去世,爸爸因眼睛失明、患有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而住院,行动不便、没有劳动能力。他有时候在学校上课,有时候在医院照顾他爸爸,如此上学上了3年。
对于像他这样经历重重困难才念到高中的孩子们,他的高中老师如此形容:“一开始你会困惑,这孩子在作业等方面怎么那么难以达到老师的要求?但等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后你会觉得,这个孩子能够上学、撑到现在,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考100分也好,60分、20分也罢,学习的要求在他身上根本就微不足道。”
蒋黎明所在的高中位于县城之外,是楠关镇上的一所县二中,曾一度处在“被撤并的危险边缘”,经过镇政府和群众基于经济发展和教育需求的强烈呼吁,才得以保留。但这所高中的生源,却是经过了市民办学校—市最好的公立学校—县一中三轮筛选后剩下的。
农村孩子进入高中及大学的比例低于城镇,其中大量是没能进入一中或超级中学的二中孩子。(图/网易数读)
被剩下的孩子和边缘化的县二中(县域内普通中学),不在少数。
调研显示,在中国,2000 多个县容纳了全国 50%以上的学生,其中优秀的县一中孩子能占多少?
剩下的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被培养、长大?他们如何面对资源的匮乏、升学的困难?
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访谈了广东、陕西、安徽、湖南、江西、河北等省7个县域的25所中小学校,历时4年(2019-2022),写成关注县域教育的《县中的孩子》,近期出版。
她向新周刊分享了她在研究中观察到的“县二中们”的情况,以及她的思考。以下是她的讲述。
曾经,每个县都有一所县二中
20世纪90年代末,我就读于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第六中学。我们那个县不算很大,却有10所高中,包括职业高中。长沙县第六中学算规模比较小的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,国家大力普及基础教育、建立基础教育学校,我们县的中学大多都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。按照地理和人口聚集的区域来分布,校名编号一二三中,当然最好的肯定是一中。
林小英就读的高中。(图/林小英提供)
20世纪90年代,在县内撤乡并镇、撤区设镇、乡变成镇的过程中,有不少县最后只剩一所高中。
2001年开始的“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”,把有限的教育资源、资金集中用到少量的学校里面,希望能够提高教育质量。这个政策初心很好,但后来被执行成了“撤点并校”。
撤点并校,初中数量下降26.19%。(图/《新闻直播间》截图)
我们可以把县里最好的中学都简称一中,其他中学都简称二中。通常,县政府出于一本上线率、清北上线人数的考量,会把更有优势的资源集中到县一中,无形中也就加剧了一中和二中们在学校规模、人员数量等方面的差距。
一中牢牢把握住了最优质的生源以及资源,老百姓用脚投票,两种力量叠加,好学校越来越好,二中类学校好像就自然衰败了。
目前,每个县的二中情况不同,大致分为:一个县里面只有一所高中;有一所最好的高中,一所非常弱的二中;有一中,还有好几所二中和职业高中,这种生态相对比较均衡。
县教育局对县城中学进行学位分配的政策倾斜,使得二中的高中生源数量和质量被“规定性”地下降了。
陕西省某县二中,位于当地一个“大镇”上,招收镇下辖的几个乡的学生,是全县唯一的完全中学(有初中和高中)。
其校长闻先生说:“省上负责划拨县的名额。我们县有3000名初中毕业学生,按照四六比(普职比),今年普高会分到1600多名学生。县上首先是要保障县城中学的规模,所以给县城划拨了1300人,只给我们拨了300人。中考满分700 分,我们收的高一新生最高成绩是 379分。”
拥有优秀学生的县一中,成为城市精英教育模式的追随者。(图/一席·林小英)
县域内的资源分配不均,直接造成了县一中与县二中的分野,这也代表了城市学校与县域学校之间的巨大差异。本质上,县一中已经是城市精英教育模式的追随者。更大的背景是:城市名校跨区招生,让所有县中都被城市学校和私立学校所夹击。
有人开玩笑说,我应该再写一本《县二中的孩子》。但我所研究的“县中”里,县一中不占大头。我关注的也不是那种超级中学里的孩子,而是在县普通中学里读书的孩子。
在我们涉足的广东、陕西、安徽、湖南、江西、河北等省份的县域来看,全县中考排名前100名的学生中,至少有一半都被所在的市、省会城市学校或私立学校“挖走”。如果再细化到中考前 20名,能留在本县就读高中的人数几乎为个位数,甚至是零。
有校长直言:“好学生全都走了,再怎么教都没有办法体现我们的工作价值。”
(图/《小欢喜》)
最近几年,随着政府加大对跨区域招生的打击,情况有所好转。2015年、2017年我去浙江调研的时候,很多学校还是可以跨区域“掐尖”的,但是今年6月,他们说已经完全禁止了(2020年浙江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行“公民同招”,2022年又出台了《浙江省山区26县和海岛县“县中崛起”行动计划》)。
在浙江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,一中与二中们的分野并不明显,主要是县内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在竞争。在中西部经济相对不那么发达的地方,没有太多社会资本补充,资源基本由政府掌握,它怎么分配,直接影响二中们怎么发展。
“四类孩子”
谁还留在县二中?我们没有具体的数据。但政策规定就近入学、听从安排,谁能够绕过安排,或者考上某个分数,那远方一定是有更好的资源等着,留下的大概就是“离场能力”相对弱的。
这种离场能力,背后是家庭资本、成绩资本。凭借家庭经济能力、孩子学习成绩或社会人脉关系等“择校资本”,孩子就能到市里的优质学校或承诺学费优惠好处的民办学校就读。家庭困难的学生,有更大的概率“滞留”在县中。
林小英《县中的孩子》于今年7月出版。
一位县二中校长将校内生活困难学生总结为四类:家庭不健全、经济极困难、(家距学校)路途很遥远、长辈需照顾。
他谈道:“我们学校的学生里,家庭情况特殊的特别多,有父母离婚的,家庭重组的,或者父母未离婚但有一方突然离家出走的。这种情况,家长往往一走就是很多年,再也没有音信。家庭正常的孩子的比例还是很少。”
“我教过一个小女孩,初中毕业后,在她大爹家、二爹家、姑姑家、姨姨家辗转。平时在学校上学,周末就在这些个亲戚家,到下一学期就换一个亲戚,再下学期再换一个亲戚。”
一线城市的孩子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学习,但县中的孩子还得承担家务甚至生活重担。一个高一学生家长说:“我整天不在家,在外面做工。我丈夫有病,做不了事情。家里还有田,暑假的时候孩子们是要去帮忙的。”
《变形计》中,12岁的梁小友带着2岁弟弟一起上课,后于高二辍学。(图/《变形计》)
我们对苦难人群的画像,往往是家里特别穷但成绩特别好,或者家里特别穷、成绩特别不好。实际上,这类人群会得到社会上各种机构的帮扶。
现实中,恰恰有大量不够困苦、成绩也不是特别好的孩子,他们不一定符合资助机构的标准。当这样的孩子刚刚够着普高线,读还是不读?就算读了普高,也不见得一定能上大学,读还是不读?
发现有学生想辍学,老师和校长如果去劝阻,家长就会问:如果再读3年要花3年钱,你觉得TA能考上大学吗?老师只能说,好歹读个高中还是有用的。但这样的话语,是多么的无力。
义务教育后农村中学的辍学率。(图/网易数读)
身处县二中,孩子和老师们遇到的问题,与在一线城市学校遇到的是不一样的,有些甚至都放不到台面上来说,他们只能从实践中、经验中去寻找方法。
在校外,他们很少会主动阅读课外书,对近在眼前的学业选择(文理分科)显得迷茫和随意。提到课余生活,就是玩手机、娱乐听歌、喝奶茶、逛逛商店、买买生活用品,快乐却单调。
他们也有手机,但现代信息设备太考验我们的信息素养(Information Literacy)了,它指数级地拉大了信息的鸿沟。有时候你觉得全世界都应该知道的一件事,某些人即便成天拿着手机也全然不知。
成年社会尚且如此,未成年人拿着手机,能抵制住游戏的诱惑吗?能克制自己不“住”在上面,建个小群跟同龄的孩子插科打诨吗?所有APP都在进行个性化推送,你想看什么就给你推什么,这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吸引力是巨大的。
(图/《小欢喜》)
一线城市的孩子运用互联网时,更懂得如何收获当下数字化经济带来的社会红利。即便县中的孩子有着相同的上网渠道,他们也缺乏必要的指导和支持,难以养成适应数字时代的头脑,无法利用互联网来给他们的人生增加机会。更多的是停留在原地,享受网综快餐以及电子游戏所给予的快感。
在一线城市,课外补习之风盛行。以北京市海淀区黄庄为代表,那里的时间被严重挤压,任何一分钟的浪费,都会被上纲上线到“影响未来的人生”。
但我们调研发现,在欠发达地区,县中里的学生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。时间被拉长,变得很缓慢,每个时间段填充的活动都很单一甚至单调。他们并不知道未来的跑道有多长,只关注眼前这一截路程上,他们要如何奔走、打发时间。
(图/纪录片《初三》)
一边是家庭密集型教养方式在一线城市越来越盛行,人们的焦虑感也越来越强;另一边,由于经济压力及学业支持方面的力不从心,放养型甚至放任型的教养方式在县中越来越普遍。
未来,这两类孩子终究要相遇,要么是在考场,要么是在招聘会。他们会如何打交道?他们用何种眼光看待对方,以及对方的孩子?
县中老师,流失与留守
近年来,二中不断地受到来自民办学校和县一中的挑战和威胁。
教师流失问题一直存在,在西部县域尤其严重。二中的师资总会向县城的一中流动,曾有一中校长毫不讳言“二中是一中教师的摇篮”。
前文提到的闻校长,在介绍二中的教师流失情况时说:“3年时间调走了 60 多个老师,基本上都是那种绝对的骨干。”
郁校长是相邻的另一所镇级初中的校长,他也说两年以前就经历了师资流动高峰期。“本来就只有50多个老师,一次调走了9个,4个教英语的都调走了。这其中并非全部都是正常调动,还有几个以所谓‘跟岗学习’名义跟到县城学校去,就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2022年2月17日,贵州省从江县刚边壮族乡中学初三年级学生在上课。(图/视觉中国)
作为一个局外人,我能理解乡村老师们的选择。人在工作之余,总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额外的滋养。但这些学校所在的地方,往往与文化资源绝缘。圈子和根基都不在这里,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,怎样对抗内心的孤独?
他们毕业于城市的学校,放假后不住在村镇里。开学后,TA如何再去面对斑驳的墙壁、阴冷的宿舍?这些是他们必须忍受的吗?
我跟着他们回到宿舍的时候,能感受到落寞感排山倒海地袭来。TA就算明天撂挑子不干了,我也能理解。
但这句我最后没写进书里,因为它不完全是学术的问题,也不完全是教育的问题。
为了解决县中老师流失多的问题,学校可以招聘一些特岗老师(这是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特殊政策,特岗教师没有编制,但是3年服务期满后,优先转入正式编制)。
目前的县普通中学老师,一部分是“那个年代的中师生”(主要是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、分配到各地中小学任教的老师),一部分是从师范类本科毕业后主动考进来的,一部分是政策性的资源补充,即特岗教师。
2020年4月10日,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民族中学学生在开班会。(图/视觉中国)
安徽省一所县级高中的200 多个老师中,50 岁以上的占40%,30 岁以下的占40%, 中间出现断层。2018、2019 年招进的 50位教师都在 30 岁以下,其中 45 位是女性。这个县里两所高中的校长都认为,教师的性别结构、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有问题。
老教师与新教师,就像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。当年中师要求教师对语数音体美等都懂一点。如今对新老师的要求,基本上以单一的学科知识和教学成绩作为衡量标准。
某二中校办的周主任试图在学校里找一名篮球比赛裁判,但发现“好像没有一个老师能当裁判”。“我们这些从中师出来的老教师,做起规则、手势来,都是很正规的。现在的体育老师根本都没教过高中学生(如何做裁判),可能他们自己都不会。”
新教师天然地认为,假设我是教数学的,就不需要当篮球裁判的本领。此外,他们也不理解体育课为什么要教学生做裁判。这些原本是中学老师捎带手就能完成的事,现在已经没有人应对了。它们最终会落到学生、家长身上,需要他们花钱上课外培训解决。
(图/《老师·好》)
原本,我们对小学老师的要求,是带孩子整体地领略这个世界、培养学生的感性认知。如果一所小学以招到硕士甚至博士作为师资优势,说明这所学校是完全不懂小学教育的。
中学阶段,教师除了要有学科素养、能教授各学科的理论知识外,还要通过学科来做规训。不仅仅是注重纪律,还要培养学生的行为规则意识与道德。比如,学生学了电学后,要知道不能随意用剪刀剪正在通电的电线;了解到硫酸的腐蚀性,就知道不能朝人脸上泼,等等。
但当下,我们特别强调不要输在起跑线上。起跑线又不断地前移,导致中学大学化、小学中学化、幼儿园小学化。每一个阶段对教师素养的要求,都被模糊了。
如今,“那个年代的中师生”可以说是全县基础教育发展的中流砥柱。比如闻校长和郁校长,家都在乡里,职业生涯都始于家门口或者家附近的镇上学校。对于本地的风土人情、社会状况、经济发展、教育生态等情况知根知底,考虑学校的教育问题时,就知道如何结合本地具体情况来分析、解决。
此前,闻校长在县城给父母买了房子。他说:“我无数次想一走了之,因为我可以到更好的学校。但是走了怎么办呢?我若离开这个地方,以后就不好意思再回来了,我没办法再回到这个家乡来,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极度的不负责任。”
理想的兜底
用市场的逻辑来看,当一中的生源、师资越来越好,产出(升学率、教育理念)也足够好,它有没有动力去帮助县里的二中?我觉得是没有的。
它更有动力去办一所民营性质的分校,提供好的硬件,输入一些办学资源,走市场化道路,这就是转制学校;甚至扩张自己,变成一个办学集团。“衡水模式”在全国各地全面开花,它是示范给二中看的吗?我觉得不是。
在大公司的垄断下,小公司要么成为它的供应商,要么就被它灭了。县域教育到底怎么办?出路在哪里?我并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。
2017年4月29日,河北保定,雄县中学。(图/视觉中国)
过去20年间,政府一直在出手干预,希望示范高中的学校真正起到示范作用,辐射、带动区域其他学校的发展。
很多城市选择把已经成型的学校重新组合,搭配初中、高中,形成一个教育集团,通过对口直升来缓解学区房焦虑。一些县让学校与学校联盟,打造资源共享和相互帮扶的体系。但这种联盟,通常由辖区内最高学段的学校来主导。这位校长掌握资源,他有可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学校,这又构成了一级资源的截流。
那把二中都变成“衡中”?大家可能认为,最令人欣慰的参照对象就是衡水中学。它有两个最显见的特征:实施半军事化管理、清北率非常高。久而久之,人们会认为这其中存在因果关联——因为军事化管理,所以升学率高。
超级中学的不同模式。(图/网易数读)
其实,大部分城市、农村的普通高中,特别是寄宿式高中,采用的都是半军事化的管理。但它们没有得到衡水那样的高升学率,人们会如何归因?可能会认为生源不行、管理不够严苛、老师还不够努力……这种追问会指向很多方面。
我们没有看到的是,衡中模式下,老师和学生的压力都非常大。衡中的老师总在钻研考题、寻找解题的套路,以节省学生自主探索时要付出的精力。我们的县二中们能学到吗?有必要那么做吗?
对于很优秀的学生来讲,也许在哪里上学都没有什么差别。反而是这些二中的孩子,是不是能接受到普遍的、统一的教育模式,我是打问号的。
2022年6月7日,正值高考,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第三中学考点,一个学校只设一个考场,一个考场仅有一名考生。(图/视觉中国)
我调研过一所衰落的县一中——P中。过去,P中初中部参加中考的学生,前100名里仅有15人能留在本校读高中。生源不好,导致连年高考成绩不好,形成恶性循环。连初中班主任都会跟学生们说,千万不要留在P中读高中。但到2022年,P中高中部的本科上线率已经达到63%。
它的改革特别简单:补上学校围墙的缺口,解决学生在洗澡时衣服被偷走的问题;提供免费早餐,让老师们愿意来监督学生早自习;把寒暑假充分利用起来,给孩子们补补课;学生的英语基础太差,就引入小语种如日语,让学生可以选择日语高考(新高考外语包含英语、俄语、日语、德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六门)等等。
教育是很朴素的事,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措施,只需要回归常规教育、回归常识。在没有那么焦虑的环境下,规范地开展教育,有些人就能成才。
2022年05月28日,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实验高中的高三学生在教室里复习备考。(图/视觉中国)
有一次,我在一个县调研结束,有10个中小学的校长和1个幼儿园的园长来与我交流。
他们提到,家境好、成绩好的学生,多数都通过各种途径离开了当地,要么进入县城最好的高中,要么去市里上学。留在镇里小学、初中念书的孩子,早就是被筛了好几遍剩下来的了。这是很多县域教育的基底,此地也不例外。
过去几年,他们已经试着放下以往对学习成绩的执念,转而思考:如何为这些注定无法升入较好大学的孩子们,提供让他们终身受用的学校教育体验。
孩子们对文化课程不是很有兴趣,就把兴趣类、动手类的课程开得有趣一些。他们还想用自己的方式出卷子来考试,让孩子们的成绩显得不那么难看……
他们问我:“林老师,我们就想听您一句话,我们这么做,您觉得可行不?”
一方面,我当然会分享多元智能理论(智能是多元的,每个人身上至少存在七项智能,即语言智能、数理逻辑智能、音乐智能、空间智能、身体运动智能、人际交往智能、自我认识智能),学习与成绩只对应其中的几个部分。
另一方面,他们手中调皮捣蛋、成绩不怎么样的孩子,也配拥有更好的生活,也可以在学校里当一个好学生,就看你的学校怎样确立“好”的标准。
(图/《十八岁的天空》)
这些老师做的,就是理想状态下县域普通中学能实现的兜底——他们熟悉几乎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,能担负起一些外出务工的父母无法履行的责任:孩子回家没人管,学校提供一些活动,让你七八点钟再回去;孩子一个人在镇上租房子住,校长出面发动其他家长合力照顾……
只是,社会上对这些学校的评价,或许会让校长们寒心。所以,我在尾声一章中写道,我们对中国基础教育事业的评价,不需要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。办学质量不能只看升学率,要考虑到在地化的情境。
另外,就是分配正义的问题。如果全县最好的资源都配给了一中,又凭什么拿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其余的学校?一部分学校承担县内精英的培养,那么另外一些学校比如县二中,就回归基础教育,帮学生的整个人生打基础。
毕竟,这将是许多人一生最后的教育阶段。
(蒋黎明、闻校长、郁校长均为化名,文中部分内容引自林小英专著《县中的孩子》))
校对:杨潮
运营:小野
排版:熊梓瑜
1.《县中的孩子》,林小英
2.《农村撤点并校需听取家长意见》,中央电视台
3.《穷人的孩子,一出生就已经输了高考》,网易数读
4.《超级中学,农村孩子高考的救命稻草》,网易数读
5.《浙江:全面推行“公民同招” 民办学校不得跨区域招生》,中国青年报
6.《浙江出台“县中崛起”行动计划,禁止跨区域“掐尖”招生》,澎湃新闻
标签: